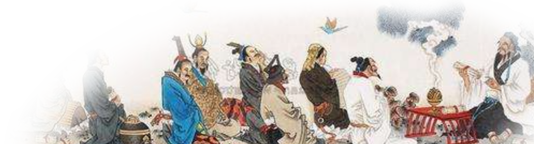http://www.hao123.com/mid/15780160348580396131
20世纪70年代末,我任教的三官庙乡,地处秦岭北麓,渭水之南,沟壑纵横,交通不便,自然条件很差,但人们对教育还是极其重视的。全乡七千多口人,十个行政村,五十二个村民小组,大小学校达十七八所,学校由村上办到了组上。一时间,师资极其短缺。大多数学校都是一个老师,一群娃娃。
1980年秋季,乡上把我调整到水凹小学任教,这所学校,先前是办在民房里,后又搬了几处地方,随着学生的增加,组上决定建座新房子,就在小村北边的一块空地上,坐北向南,建起四间瓦屋,村上的工匠,板打的四堵土墙,木料是从坡上伐的,砖瓦自己烧的,学校很快就建成了。
单人独校,一至三年级,学生六十多名。上学来的有本村的娃娃,还有邻村的几个娃。我一个人,是校长,又是老师。哨音一响,上课了,一个教室,我先让高年级学生复习上节课的内容,给低年级学生讲。偶尔有高年级学生用心听低年级的课,入神了,猛地站起来回答问题,弄得全班哄堂大笑。慢慢时间久了,就进入了常态化,高年级学习好的同学,把老师讲的都默记于心,上自习时,踊跃地替老师辅导低年级的同学,发挥小老师的作用,维护着全班的纪律和秩序。
放学后,我目送着孩子们离开学校。这时,母亲的饭还没做好,我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看书,备课。饭做好了,母亲站在大树下喊我,我才恋恋不舍放下手中的书或笔,跑出办公室。匆匆地回家,端起母亲盛好的饭,和母亲谈着与学生间发生的趣事。
孩子们在家吃完饭,就往学校跑。他们在场院里,滚铁环,踢沙包,玩得开心,使整个小村都有了生机与活力。上自习了,我坐在他们中间,指导他们写字,算数学题,他们鸦雀无声,有的用小眼睛偷偷瞄着我。后来,我在办公室的墙上,正对门的地方,挂了块大点的镜子,时刻监控他们在教室里的一举一动。起初,孩子们很不习惯,但渐渐地适应了,自习时,我在他们身边与不在,基本上都能保持一致。守纪律,用心学。连村里的乡亲们都说:“你把咱村里娃娃给管住了,知道学习,懂事了。”
我不会音乐,为了让学生学到新歌曲,我借了一台收音机,组织学生坚持听《每周一歌》,并把歌词用毛笔抄写在一张大白纸上,贴在黑板边上,与学生共同学唱;同时,还组织学生收听《小喇叭》等节目,丰富他们的课间生活。
冬天,地里的农活少了,常有乡亲们来串门,围着火炉,翻看着报纸和杂志,与我谈论村里村外的趣事,或交流他们生活中的苦衷与无奈。我为他们砌一块砖茶,放到壶里煮酽,边喝边聊。不知不觉,夜就深了,送走他们,我睡意全无,独自一个人在漆黑场院里徘徊,远处沟畔传来阵阵狐狸和狼的嚎叫声,但我并未感到恐惧和凄凉,我大声朗诵着陆游的诗句:“莫笑农家腊酒浑,丰年留客足鸡豚。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
初雪的清晨,孩子们早早来到学校,手里拎着用搪瓷盆或破缸子做的火炉,教室的门还未开,他们就在我办公室窗前的墙角挤着取暖。我急忙起床打开教室门,帮孩子们把火盆里的火拨旺,让他们一边烤着火,一边晨读。凛冽的北风,带着哨音拍打着窗户,窗上的塑料薄膜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,但教室里却温暖如春。
那些年,一下起雪,就是好多天。远处山峦,近处田野、树木、房舍、山路,都被厚厚的雪覆盖。村上的男女老幼,齐动手,清扫积雪,先把孩子们上学的路扫干净,再扫主干道路。有线广播不停地传来公社领导的最新指示,督促人民群众抓紧清扫积雪。我站在校门前的场院里,把学生接进教室,那时的日子都很苦,娃们穿的都单薄,十个娃有九个都穿着从街上买来的旧棉鞋。我给他们把火搭旺,烤暖和了,再让他们做作业。
下雪天,正赶上全乡期末统考,考点设在五六里路外的胡寨小学,风吹,雪飘,路滑,大学生帮小学生,体质弱点的小娃,就让家人护送,实在有困难的,我就背上去考,就这样,还有不慎滚成“雪球”的。有时候,冬季考试,乡上把考点设在各村小,让全乡的老师交换监考。我的水凹小学居然在全乡组织的统考中,三个年级六门统考科目,四门名列全乡第一,另两门也居前列,年终评奖会上,教肓专干用浑厚的男中音说道:“水凹学校考这成绩,值得大家深思,值得学习!”至今还在脑海回响,记忆犹新,感觉就似发生在昨天。
现如今,年轻人纷纷离开山村,奔向了城市。学生也随之流动,山村出现了一个老师或几个老师、几个娃的荒凉景象。这也许是在城市化与乡村的撕扯中,乡村教育出现的暂时的阵痛,我相信不久的未来,乡村教育一定会有新的发展。现在每次回家,我都要到村学校去看看,寻找那些过往的岁月留下的印痕。因为,我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忙碌的日子,也是一段富有诗意的时光。种地,读书,进修,娶妻,生子等有许多发生在这山坳里的故事。我曾在痛苦中挣扎,在迷茫中徘徊,但未放弃,执著前行。一个老师,一所学校,一群娃娃的那段日子,很苦,很累。但也很充实、很快乐、很难忘、很美好。虽已远去,但令我久久怀念。